數學大師與成大師生分享研求之樂 丘成桐院士說:做科研要付出代價,卻快樂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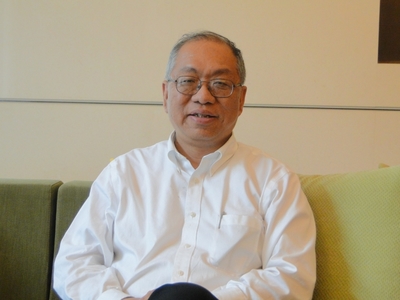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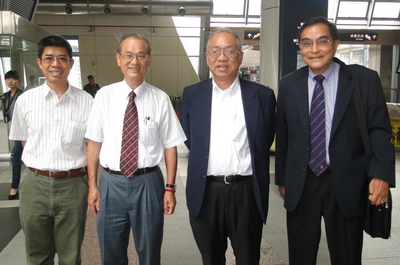
【台南訊】即將於5日接受成功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的1982年費爾茲獎(Fields Medal-相當於數學界諾貝爾獎)得主、亦被世界公認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數學家之一的丘成桐院士,4日在成大資深執行副校長馮達旋的陪同下提前抵達成大,隨後並在成大格致廳與擠爆會場的數百名成大師生分享「研求之樂」。他說,做科研雖要付出代價,卻是快樂無窮。
獲得費爾茲獎的兩位華人之一的丘成桐院士,是一位相當迷樣的科學家,在他的身上除看到偉大數學家的身影,也能看到大文學家的風範,研究數學之外,他還飽讀經書,學富五車,擁有豐富的文學素養,他愛看紅樓夢,背誦秦漢和六朝的古文,讀司馬遷的自傳、報任安書、李陵答蘇武書、陶淵明的歸去來辭、歌德的浮士德等等文章。在他演講過程中,經常引經據典;文天祥「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元稹「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韓愈「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等名言,朗朗上口,讓人折服。
丘成桐院士表示,閱讀紅樓夢,深刻感受到曹雪芹深入細致的文筆,絲絲入扣地將不同的人物、情景,想像作者的胸懷和澎湃豐富的感情,也常常想像在數學中如果能夠創作同樣的結構,是怎樣偉大的事情。他認為感情澎湃,不能自己,就能夠將學者帶進新的境界。
他認為立志要做大學問,只不過是一剎那間事、而感情的培養是做大學問最重要一部份。自己年少時,喜歡在元朗的平原上嬉戲玩耍,也在沙田的山丘和海濱遊戲。與同伴在一起,樂也融融,甚至逃學半年之久。真可謂倘佯於山水之間,放浪形骸之外。他說,在那期間,唯一的負擔是父親要求讀書練字,背誦古文詩詞,讀近代的文選,也讀西方的作品。但是當時我喜愛的不是這些書,而是武俠小說,從梁羽生到金庸的作品都看了一遍。
除武俠小說外,還有薛仁貴征東、征西、七俠五義,和一些禁書,都是偷偷的看,至於名著如水滸傳、三國傳義、紅樓夢等則是公開的閱讀,因為這是父親認為值得看的好書。他要求我看這些書的同時,還要將書中的詩詞記熟。這可不容易,雖然現在還記得其中一些詩詞,例如黛玉葬花詩和諸葛亮祭周瑜的文章等,但大部份還是忘記了。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很快就引起我的興趣,但是讀紅樓夢時僅看完前幾回,就沒有辦法繼續看下去。一直到父親去世後,才將這本書仔細的讀過一遍,也開始背誦其中的詩詞。由於父親的早逝、家庭的衰落,與書中的情節共鳴,開始欣賞而感受到曹雪芹深入細致的文筆,絲絲入扣地將不同的人物、情景,逐步描寫出舊社會的一個大悲劇。
父親去世以前,我學習了不少知識,也讀了不少好文章。但他的去世,卻深深地觸動了我的感情。我讀紅樓夢,背誦秦漢和六朝的古文,讀司馬遷的自傳、報任安書、李陵答蘇武書、陶淵明的歸去來辭等等文章,這些文章的內容都深深地印記在我的腦海中。文天祥說:「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足可以描述我當時讀書的境況。除了中國文學外,我也讀西方的文學,例如歌德的浮士德。這本歌劇描述博士浮士德的苦痛,與紅樓夢相比,一是天才的苦痛,一是凡人的苦痛。描寫苦痛的極至,竟可以說得上是壯美的境界,足以移動人的性情。
由於父親的去世和閱讀文學的書籍,這大半年感情的波動,使我做學問的興趣忽然變得極為濃厚,再無反顧。凡人都有悲哀失敗的時候,有人發憤圖強,有人則放棄理想以終其身。黃仲則詩:「結束鉛華歸少作,屏除絲竹入中年,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着鞭。」詩雖感人,思想畢竟頹廢,使人覺得陰雲蔽天。難怪黃仲則一生潦倒,終無所獲。反觀太史公司馬遷,慘受腐刑,喟然而嘆「身毀不用矣」。卻完成了傳誦千古的史記,適可藏諸名山大都。他在自傳中說:「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後,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太史公的挫敗和鬱結,反而使他志氣更為宏大。
四十年來我研究學問,處事為人,屢敗屢進,未曾氣餒。這種堅持的力量,當可追索到當日感情之突破。我一生從未放棄追尋至真至美的努力,可以用元稹的詩來描述:「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當遇到困難時,我會想起韓愈的文章:「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我也喜歡用左傳中的兩句來勉勵自己:「左輪朱殷,豈敢言病。」此句出自左傳晉齊鞍之戰:「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敗君之大事也。』」
做研究生時,我有一個想法,微分幾何畢竟是牽涉及分析﹙即用微積分為工具﹚和幾何的一門學問,幾何學家應該從分析著手研究幾何。況且微分方程的研究已經相當成熟,這個研究方向大有可為。雖然一般幾何學家視微分方程為畏途,我決定要將這兩個重要理論結合,讓幾何和分析都表現出它們內在的美。在柏克萊的第一年我跟隨Morrey教授學習偏微分方程,當時並不知道他是這個學科的創始者之一。從他那裏我掌握了橢圓形微分方程的基本技巧。在研究院的第二年我才開始跟隨導師陳省身先生學習複幾何。
畢業後,在我的學生和朋友Schoen、Simon、鄭紹遠、Uhlenbeck、Hamilton、Taubes、Donaldson、Peter Li等人的合作下,逐漸將幾何分析發展成一個重要的學科,也解決了很多重要的問題。這是一種奇妙的經驗,每一個環節都要花上很多細致的推敲,然後才能夠將整個畫面構造出來,正如曹雪芹寫作紅樓夢一樣。尼采說:「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曹雪芹說:「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非尋常。」
我們眾多朋友創作的幾何分析,也差不多花了十年才成功奠基。不敢說是「以血書成」,但每一次的研究都很花費工夫,甚至廢寢忘餐,失敗再嘗試,嘗試再失敗,經過不斷的失敗,最後才見到一幅美麗的圖畫。簡潔有力的定理使人喜悅,就如讀詩經和論語一樣,言短而意深。有些定理,孤芳自賞。有些定理卻引起一連串的突破,使我們對數學有更深入的認識。每一個數學家都有自己的品味和看法,我本人則比較喜歡後一類數學。當定理證明後,我們會覺得整個奮鬥的過程都是有意思的,正如智者垂竿,往往大魚上釣後,又將之放生,釣魚的目的就是享受與魚比試的樂趣,並不在乎收穫。
從數學的歷史看,只有有深度的理論才能夠保存下來。千百年來,定理層出不窮,但真正名留後世的結果卻是鳳毛麟角,這是因為有新意的文章實在不多,有時即使有新意,但是深度不夠,也很難傳世。當年我看武俠小說,很是興奮,也很享受,但是很快就忘記了。在閱讀有深度的文學作品時,卻有不同的感覺。有些武俠小說雖然很有創意,但結構不夠嚴謹,有很多不合理的元素,與現實相差太遠,最終不能沁人心脾。我們幾個朋友在研究和奮鬥程過中,始終不搞太抽象的數學,總願意保留大自然的真和美。
王國維評古詩十九首「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久貧賤,轗軻長苦辛。」,以為其言淫鄙,但從美學的觀點,卻不失其真。數學創作也如寫小說,總不能遠離實際。紅樓夢能夠扣人心弦,乃是因為這部悲劇描述出家族的腐敗、社會的不平、青春的無奈,是一個普羅眾生的問題。好的數學也應當能接觸到大自然中各種不同的現象才能夠深入,才能夠傳世。
今日有些名教授,著作等身,汗牛充棟,然而內容往往脫離現實。一生所作,不見得比得上一些內容與實際有關的小品文,數十載後讀之,猶可回味。我自己做研究,有時也會玄思無際,下筆滔滔,過了幾個月後才知空談無益,不如學也。在這時,總會想起張先的詞,「尋恨細思,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我的研究工作,深受物理學和工程學的影響,這些科學提供了數學很重要的素材。廣義相對論就是一個重要的例子。一九七三年在史丹福大學參加一個國際會議時,我對某個廣義相對論的重要問題發生興趣,它跟幾何曲率和廣義相對論質量的基本觀念有關,我鍥而不捨地思考,終於在七八年和學生Schoen一同解決了這個重要的問題。這些與相對論有關的幾何問題始終使我喜悅。
也許是受到王國維評詞的影響,我認為數學家的工作不應該遠離大自然的真和美。直到現在我還在考慮質量的問題,它有極為深入的幾何意義。沒有物理上的看法,很難想像單靠幾何的架構,就能夠獲得深入的結果。廣義相對論中的品質與黑洞理論都有很美的幾何意義。其實西方文藝復興的一個重要反思就是復古,重新接受希臘文化真與美不可割裂的觀點。
中國古代文學的美和感情是極為充沛的,先秦兩漢的思想和科技與西方差可比擬。清代以還,美術文學不發達,科學亦無從發展。讀書則以考証為主,少談書中內容,不逮先秦兩漢唐宋作者的熱情澎湃。若今人能夠回復古人的境界,在科學上創新當非難事。除了看紅樓夢外,我也喜歡看史記、漢書。這些歷史書不單發人深省,文筆通暢,甚至啟發我做學問的方向。
由於史家寫實,氣勢磅礡,蕩氣迴腸,使人感動。歷史的事實教導我們在重要的時刻如何做決斷。做學問的道路往往是五花百門的,走甚麼方向卻影響了學者的一生。複雜而現實的歷史和做學問有很多類似的地方,歷史人物做的正確決斷,往往能夠提供學者選擇問題一個良好的指南針。王國維說學問第一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做好的工作,總要放棄一些次要的工作,如何登高望遠,做出這些決斷,大致上建基於學者的經驗和師友的交流上。然而對我而言,歷史的教訓卻是很有幫助的。
我剛畢業時,蒙幾何學家西門斯邀請到紐約石溪做助理教授。當時石溪聚集了一群年青而極負聲望的幾何學家,在度量幾何這個領域上可說是世界級重鎮。我在那裏學了不少東西。一年後又蒙奧沙文教授邀請我到史丹福大學訪問,接着史丹福大學聘請我留下來。但是當時史丹福大學基本上沒有做幾何學的教授,我需要做一個決定。這時記起史記敍述漢高祖的事蹟。劉邦去蜀,與項羽爭霸,屢敗屢戰。猶駐軍中原,無意返蜀,竟然成就了漢家四百多年的天下。對我來說,度量幾何的局面太小,而史丹福大學能夠提供的數學前景宏大得多,所以決定還是留在史丹福做教授,與Schoen、Simon合作。現在想來,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如上所言,我的想法和一般同學的想法不大一樣,也不見得是其他一流數學家的想法。但是有一點是所有學者都有的共同點:努力學習,繼承前人努力得來的成果,不斷的向前摸索。我年少時受到父親的鼓勵,對求取知識有濃烈的興趣,對大自然的現象和規律都很好奇,想去瞭解,也希望能夠做一些有價值的工作,傳諸後世。我很喜愛以下兩則古文:孔子:「君子疾沒世而不稱焉。」曹丕《典論論文》:「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藉,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立志當然是一個好的開始,但是如何做好學問卻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有幸得到好的數學老師指導。當我學習平面幾何時,我才知道數學的美,也詫異於公理邏輯的威力。
因為對幾何的興趣,我做習題時都很成功,也從解題的過程中產生了濃厚的好奇心。我開始尋找新的題目,去探討自己能夠想像的平面幾何現象。每天早上坐火車上學時我也花時間去想,這種練習對我以後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中學時的訓練對同學們都有很大的好處,培正中學出了不少數學名家。我們中學的老師在代數和數論方面的涉獵比較少,培正同學們在這方面的成就也相對的比較弱,由此可以看到中學教育的重要性。
屈原說:「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文章的格調和對學術的影響力與「內美」有關,可以從詩詞、禮、樂、古文、大自然的環境中培養吸收。
但修能卻需要浸淫於書本,從聽課和師友交流中,可以發現那些研究方向最為合適。找到理想的方向後,就需要勇往直前。有理想的方向後,還需要尋找好的問題。西方哲人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在名著《形而上學》書中說:「人類開始思考直接觸目不可思議的東西而或驚異……而抱着疑惑,所以由驚異進於疑惑,始發現問題。」驚異有點像驚豔,但這種驚異一方面需要多閱歷,一方面需要感情充沛,才能夠產生。
空間曲率的概念對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我從廣義相對論中知道所謂Ricci曲率的重要性。通過愛因斯坦方程,它描述物質的分佈,這個方程的簡潔和美麗使我詫異。我認為了解Ricci曲率是了解宏觀幾何的最重要一環,但幾何茫茫,無從著手。有一天很高興地發現Calabi先生在一九五四年時有一篇文章,敍述在複幾何的領域中,Ricci曲率有一個漂亮的命題,但他卻沒有辦法証明這個命題。當時我很興奮,但也覺得它不大可能是真實的,因為這個命題實在太美妙了。所有年青的朋友都是這麼說,甚至我的導師也是這麼說。
陳省身老師甚至認為這個研究方向的意義不大,我卻固執的認為對Calabi猜測總要找出一個水落石出的答案。直到有一天,經過大量的嘗試後,我才發覺從前走的方向完全是錯誤的,於是反過來企圖証明這個猜想。但要証明它,卻需要有基本的分析能力,我和我的朋友鄭紹遠花了不少工夫去建立跟這個問題有關的工作,終於我在一九七六年完成了這個重要猜想的証明。這個猜想在一九七六年全部完成,我同時應用它解決了代數幾何裏好幾個基本問題。毫無疑問的,這是一個漂亮的定理,也打開了幾何分析的一個大門。
當時我剛結婚,正在享受人生美好的時刻,也獨自地欣賞這個剛完成的定理的真實和美麗,有如自身的個體融入大自然裏面。當時的心境可以用下面兩句來描述:「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由這個定理引起的學問,除了幾何分析上的Monge-Ampere方程外,在代數幾何上獨樹一幟,以後在弦學理論成為一個重要的宇宙模型。
在解決Calabi猜想的同時,有一天我碰見到從前在柏克萊的同學Meeks先生。他是一個嬉皮士,兩手各摟抱着一個少女,在系裏的走廊上高高興興地走來。但我覺得此人極有才華,建議與他合作去解決一個極小流形的古老問題。我們用拓撲學的辦法解決了這個問題,反過來又用得到的結果,解決了拓撲學上一些重要的問題,再加上我的同學Thurston的重要工作,竟然解決了拓樸學上著名的Smith猜想。一九七六年可說是我收獲極為豐富的一年,我那年剛結婚,剛搬到洛杉磯,生活未算安定。由此可知,做學問不一定需要最安定的環境也可以成功的。
在代數幾何得到一定成功後,我接觸到很多代數幾何學家,也開始瞭解這個學科的走向。Calabi猜想是關於度量的猜測,我開始比較度量幾何和複纖維叢上的度量問題,我猜想纖維叢也有類似於Calabi猜想中的度量,同時和纖維朿的穩定性有關,Uhlenbeck和我花了很長一段工夫才將這個問題全部解決。﹙在這期間英國的Simon Donaldson用不同的方法解決了二維的情形,並且很快就完成了高維空間中這個定理的重要情形。﹚在完成這個問題後,我建議我的朋友Witten考慮這個定理的物理意義,他當時認為這個定理的物理意義不大,但一年後他改變了想法,寫了一篇文章解釋它們在弦論上的作用。直到如今,這個結構在弦論上仍佔據着很重要的位置。
這篇文章花了Uhlenbeck和我很長的時間,可說是極為艱苦的奮鬥才完成的。Uhlenbeck來Princeton訪問我時,為了尋找這個問題的解法,竟然關在房間裏三天之久。我和Uhlenbeck的工作以後被推廣,尤其是加上我的朋友Hitchin引進的Higgs Field以後,成為代數幾何和算術幾何中強有力的工具。Calabi猜想的一個重要結論是,代數空間有很強的拓樸限制,包括Miyaoka-Yau不等式的成立,從而有代數流型的剛性結果。這個結果被我應用而解決了古老的Severi猜想。在這個基礎上,我猜測某些代數空間有更一般的剛性結果。我並提出用調和映射的方法來解決這個猜想。
其實在更早的時候,我和Schoen已經在調和映射做了不少工作,例如在群作用的問題。當我向蕭蔭堂先生提出我的猜想和解決的辦法時,他開始時並不相信這個方法的可行性,但是他還是遁着這個路徑去解決了我猜想的一部份。以後Jost和我,以及蕭蔭堂和他的合作者們更成功地將調和映射應用到一些更經典的剛性問題上去。在一九八四年弦理論成為理論物論的重要一門學科以後,我以前做的好幾個工作都受到理論物理學家的歡迎。我也深受物理學家對數學洞察力的影響,我有十多位跟隨我的博士後,他們都是物理學博士。我從他們那裏學習物理。
最令我驚訝的一次是,我的博士後Brian Greene跑到我的辦公廳,向我解釋他最新的發現,就是在Calabi-Yau空間中,存在所謂鏡對稱的觀點,這個發現對代數幾何有極大的衝擊,影響至今。它的結論至為漂亮,從不同角度解釋了代數幾何裏百年來不解的現象,但物理學家沒有辦法給出一個証明,六年後在眾多數學家努力的基礎上,劉克峰、連文豪和我終於找到一個滿意的証明。但是我覺得我們對鏡對稱這個現象還是沒有得到深入的瞭解,兩年後Strominger、Zaslow和我終於找到這個對稱的幾何解釋,引起了一連串重要的突破,可是,鏡對稱在數學上到現在還沒有嚴格的証明。Zaslow是跟隨我的博士後,他以後成為西北大學的大教授。當時我和他還做了一個重要的工作。從弦學上膜的觀點,我們找到一個公式﹙Yau-Zaslow公式﹚。這個公式可以用來計算K3曲面上的有理曲線的個數,公式由數論中的某些著名的函數給出,這是數論函數出現在計算曲線數目的第一次,以後很多代數幾何學家繼續這個研究,將這個公式推廣到更一般的情形。
與物理學家合作是愉快的經驗,可以有跳躍性的進展,而又不停的去反思,希望能夠從數學上解釋這些現象,在這個過程中往往推進了數學的前沿。過去二十多年,我也花了一些工夫去做應用數學的工作,一方面和金芳蓉在圖論上的合作,一方面和我弟弟共同研究控制理論。近年來更和顧險峰等合作做圖像處理的研究。這些工作都和我從前研究的幾何分析有關,尤其是我和Peter Li研究的特徵函數的問題。起源於當年我在史丹福研究調和函數的梯度估計。我還記得我傍晚時躲在辦公室裏,試驗用不同的函數來算這些估值,捨不得去看史丹福校園落日的景色。
史丹福的校園確是漂亮,黃昏時在大教堂的廣場,在長長的迴廊上散步。看着落日鎔金,青草連天的景色,心情特別舒暢。我早年的工作都在這裏孕育而成。除了Calabi猜想外,還有正質量猜想的証明。七九年的夏天,我和Schoen住在他女朋友Los Altos的家裏,白天我們將這個猜想的証明逐步寫出來,到了晚上十時多才回家去游泳池游泳。在這一段日子裏,我們也將正數值曲率空間的理論完成。
丘成桐院士簡歷:
1949年4月4日出生於廣東省汕頭市。師事數學大師陳省身先生,為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史丹福大學、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現任哈佛大學講座教授。曾獲卡迪獎、威伯倫獎、數學界最高榮譽之渥爾夫數學獎、費爾茲獎、麥克阿瑟獎、瑞典皇家學院頒發之克瑞福特獎,及美國總統親頒國家科學獎等重要獎項。 為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海外院士、俄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以及義大利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同時榮獲多所知名大學的榮譽博士及榮譽教授。發表數百篇學術論文及著作,解決許多著名的難題,開創許多新的研究方向及領域。他的研究工作主導了微分幾何及其它幾個重要數學領域過去三十年的主要發展。他的工作改變並擴展了人們對偏微分方程在微分幾何中的作用和理解,並影響了拓撲學、代數幾何、表示理論、廣義相對論等領域。
獲得費爾茲獎的兩位華人之一的丘成桐院士,是一位相當迷樣的科學家,在他的身上除看到偉大數學家的身影,也能看到大文學家的風範,研究數學之外,他還飽讀經書,學富五車,擁有豐富的文學素養,他愛看紅樓夢,背誦秦漢和六朝的古文,讀司馬遷的自傳、報任安書、李陵答蘇武書、陶淵明的歸去來辭、歌德的浮士德等等文章。在他演講過程中,經常引經據典;文天祥「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元稹「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韓愈「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等名言,朗朗上口,讓人折服。
丘成桐院士表示,閱讀紅樓夢,深刻感受到曹雪芹深入細致的文筆,絲絲入扣地將不同的人物、情景,想像作者的胸懷和澎湃豐富的感情,也常常想像在數學中如果能夠創作同樣的結構,是怎樣偉大的事情。他認為感情澎湃,不能自己,就能夠將學者帶進新的境界。
他認為立志要做大學問,只不過是一剎那間事、而感情的培養是做大學問最重要一部份。自己年少時,喜歡在元朗的平原上嬉戲玩耍,也在沙田的山丘和海濱遊戲。與同伴在一起,樂也融融,甚至逃學半年之久。真可謂倘佯於山水之間,放浪形骸之外。他說,在那期間,唯一的負擔是父親要求讀書練字,背誦古文詩詞,讀近代的文選,也讀西方的作品。但是當時我喜愛的不是這些書,而是武俠小說,從梁羽生到金庸的作品都看了一遍。
除武俠小說外,還有薛仁貴征東、征西、七俠五義,和一些禁書,都是偷偷的看,至於名著如水滸傳、三國傳義、紅樓夢等則是公開的閱讀,因為這是父親認為值得看的好書。他要求我看這些書的同時,還要將書中的詩詞記熟。這可不容易,雖然現在還記得其中一些詩詞,例如黛玉葬花詩和諸葛亮祭周瑜的文章等,但大部份還是忘記了。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很快就引起我的興趣,但是讀紅樓夢時僅看完前幾回,就沒有辦法繼續看下去。一直到父親去世後,才將這本書仔細的讀過一遍,也開始背誦其中的詩詞。由於父親的早逝、家庭的衰落,與書中的情節共鳴,開始欣賞而感受到曹雪芹深入細致的文筆,絲絲入扣地將不同的人物、情景,逐步描寫出舊社會的一個大悲劇。
父親去世以前,我學習了不少知識,也讀了不少好文章。但他的去世,卻深深地觸動了我的感情。我讀紅樓夢,背誦秦漢和六朝的古文,讀司馬遷的自傳、報任安書、李陵答蘇武書、陶淵明的歸去來辭等等文章,這些文章的內容都深深地印記在我的腦海中。文天祥說:「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足可以描述我當時讀書的境況。除了中國文學外,我也讀西方的文學,例如歌德的浮士德。這本歌劇描述博士浮士德的苦痛,與紅樓夢相比,一是天才的苦痛,一是凡人的苦痛。描寫苦痛的極至,竟可以說得上是壯美的境界,足以移動人的性情。
由於父親的去世和閱讀文學的書籍,這大半年感情的波動,使我做學問的興趣忽然變得極為濃厚,再無反顧。凡人都有悲哀失敗的時候,有人發憤圖強,有人則放棄理想以終其身。黃仲則詩:「結束鉛華歸少作,屏除絲竹入中年,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着鞭。」詩雖感人,思想畢竟頹廢,使人覺得陰雲蔽天。難怪黃仲則一生潦倒,終無所獲。反觀太史公司馬遷,慘受腐刑,喟然而嘆「身毀不用矣」。卻完成了傳誦千古的史記,適可藏諸名山大都。他在自傳中說:「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後,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太史公的挫敗和鬱結,反而使他志氣更為宏大。
四十年來我研究學問,處事為人,屢敗屢進,未曾氣餒。這種堅持的力量,當可追索到當日感情之突破。我一生從未放棄追尋至真至美的努力,可以用元稹的詩來描述:「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當遇到困難時,我會想起韓愈的文章:「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我也喜歡用左傳中的兩句來勉勵自己:「左輪朱殷,豈敢言病。」此句出自左傳晉齊鞍之戰:「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敗君之大事也。』」
做研究生時,我有一個想法,微分幾何畢竟是牽涉及分析﹙即用微積分為工具﹚和幾何的一門學問,幾何學家應該從分析著手研究幾何。況且微分方程的研究已經相當成熟,這個研究方向大有可為。雖然一般幾何學家視微分方程為畏途,我決定要將這兩個重要理論結合,讓幾何和分析都表現出它們內在的美。在柏克萊的第一年我跟隨Morrey教授學習偏微分方程,當時並不知道他是這個學科的創始者之一。從他那裏我掌握了橢圓形微分方程的基本技巧。在研究院的第二年我才開始跟隨導師陳省身先生學習複幾何。
畢業後,在我的學生和朋友Schoen、Simon、鄭紹遠、Uhlenbeck、Hamilton、Taubes、Donaldson、Peter Li等人的合作下,逐漸將幾何分析發展成一個重要的學科,也解決了很多重要的問題。這是一種奇妙的經驗,每一個環節都要花上很多細致的推敲,然後才能夠將整個畫面構造出來,正如曹雪芹寫作紅樓夢一樣。尼采說:「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曹雪芹說:「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非尋常。」
我們眾多朋友創作的幾何分析,也差不多花了十年才成功奠基。不敢說是「以血書成」,但每一次的研究都很花費工夫,甚至廢寢忘餐,失敗再嘗試,嘗試再失敗,經過不斷的失敗,最後才見到一幅美麗的圖畫。簡潔有力的定理使人喜悅,就如讀詩經和論語一樣,言短而意深。有些定理,孤芳自賞。有些定理卻引起一連串的突破,使我們對數學有更深入的認識。每一個數學家都有自己的品味和看法,我本人則比較喜歡後一類數學。當定理證明後,我們會覺得整個奮鬥的過程都是有意思的,正如智者垂竿,往往大魚上釣後,又將之放生,釣魚的目的就是享受與魚比試的樂趣,並不在乎收穫。
從數學的歷史看,只有有深度的理論才能夠保存下來。千百年來,定理層出不窮,但真正名留後世的結果卻是鳳毛麟角,這是因為有新意的文章實在不多,有時即使有新意,但是深度不夠,也很難傳世。當年我看武俠小說,很是興奮,也很享受,但是很快就忘記了。在閱讀有深度的文學作品時,卻有不同的感覺。有些武俠小說雖然很有創意,但結構不夠嚴謹,有很多不合理的元素,與現實相差太遠,最終不能沁人心脾。我們幾個朋友在研究和奮鬥程過中,始終不搞太抽象的數學,總願意保留大自然的真和美。
王國維評古詩十九首「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久貧賤,轗軻長苦辛。」,以為其言淫鄙,但從美學的觀點,卻不失其真。數學創作也如寫小說,總不能遠離實際。紅樓夢能夠扣人心弦,乃是因為這部悲劇描述出家族的腐敗、社會的不平、青春的無奈,是一個普羅眾生的問題。好的數學也應當能接觸到大自然中各種不同的現象才能夠深入,才能夠傳世。
今日有些名教授,著作等身,汗牛充棟,然而內容往往脫離現實。一生所作,不見得比得上一些內容與實際有關的小品文,數十載後讀之,猶可回味。我自己做研究,有時也會玄思無際,下筆滔滔,過了幾個月後才知空談無益,不如學也。在這時,總會想起張先的詞,「尋恨細思,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我的研究工作,深受物理學和工程學的影響,這些科學提供了數學很重要的素材。廣義相對論就是一個重要的例子。一九七三年在史丹福大學參加一個國際會議時,我對某個廣義相對論的重要問題發生興趣,它跟幾何曲率和廣義相對論質量的基本觀念有關,我鍥而不捨地思考,終於在七八年和學生Schoen一同解決了這個重要的問題。這些與相對論有關的幾何問題始終使我喜悅。
也許是受到王國維評詞的影響,我認為數學家的工作不應該遠離大自然的真和美。直到現在我還在考慮質量的問題,它有極為深入的幾何意義。沒有物理上的看法,很難想像單靠幾何的架構,就能夠獲得深入的結果。廣義相對論中的品質與黑洞理論都有很美的幾何意義。其實西方文藝復興的一個重要反思就是復古,重新接受希臘文化真與美不可割裂的觀點。
中國古代文學的美和感情是極為充沛的,先秦兩漢的思想和科技與西方差可比擬。清代以還,美術文學不發達,科學亦無從發展。讀書則以考証為主,少談書中內容,不逮先秦兩漢唐宋作者的熱情澎湃。若今人能夠回復古人的境界,在科學上創新當非難事。除了看紅樓夢外,我也喜歡看史記、漢書。這些歷史書不單發人深省,文筆通暢,甚至啟發我做學問的方向。
由於史家寫實,氣勢磅礡,蕩氣迴腸,使人感動。歷史的事實教導我們在重要的時刻如何做決斷。做學問的道路往往是五花百門的,走甚麼方向卻影響了學者的一生。複雜而現實的歷史和做學問有很多類似的地方,歷史人物做的正確決斷,往往能夠提供學者選擇問題一個良好的指南針。王國維說學問第一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做好的工作,總要放棄一些次要的工作,如何登高望遠,做出這些決斷,大致上建基於學者的經驗和師友的交流上。然而對我而言,歷史的教訓卻是很有幫助的。
我剛畢業時,蒙幾何學家西門斯邀請到紐約石溪做助理教授。當時石溪聚集了一群年青而極負聲望的幾何學家,在度量幾何這個領域上可說是世界級重鎮。我在那裏學了不少東西。一年後又蒙奧沙文教授邀請我到史丹福大學訪問,接着史丹福大學聘請我留下來。但是當時史丹福大學基本上沒有做幾何學的教授,我需要做一個決定。這時記起史記敍述漢高祖的事蹟。劉邦去蜀,與項羽爭霸,屢敗屢戰。猶駐軍中原,無意返蜀,竟然成就了漢家四百多年的天下。對我來說,度量幾何的局面太小,而史丹福大學能夠提供的數學前景宏大得多,所以決定還是留在史丹福做教授,與Schoen、Simon合作。現在想來,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如上所言,我的想法和一般同學的想法不大一樣,也不見得是其他一流數學家的想法。但是有一點是所有學者都有的共同點:努力學習,繼承前人努力得來的成果,不斷的向前摸索。我年少時受到父親的鼓勵,對求取知識有濃烈的興趣,對大自然的現象和規律都很好奇,想去瞭解,也希望能夠做一些有價值的工作,傳諸後世。我很喜愛以下兩則古文:孔子:「君子疾沒世而不稱焉。」曹丕《典論論文》:「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藉,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立志當然是一個好的開始,但是如何做好學問卻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有幸得到好的數學老師指導。當我學習平面幾何時,我才知道數學的美,也詫異於公理邏輯的威力。
因為對幾何的興趣,我做習題時都很成功,也從解題的過程中產生了濃厚的好奇心。我開始尋找新的題目,去探討自己能夠想像的平面幾何現象。每天早上坐火車上學時我也花時間去想,這種練習對我以後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中學時的訓練對同學們都有很大的好處,培正中學出了不少數學名家。我們中學的老師在代數和數論方面的涉獵比較少,培正同學們在這方面的成就也相對的比較弱,由此可以看到中學教育的重要性。
屈原說:「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文章的格調和對學術的影響力與「內美」有關,可以從詩詞、禮、樂、古文、大自然的環境中培養吸收。
但修能卻需要浸淫於書本,從聽課和師友交流中,可以發現那些研究方向最為合適。找到理想的方向後,就需要勇往直前。有理想的方向後,還需要尋找好的問題。西方哲人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在名著《形而上學》書中說:「人類開始思考直接觸目不可思議的東西而或驚異……而抱着疑惑,所以由驚異進於疑惑,始發現問題。」驚異有點像驚豔,但這種驚異一方面需要多閱歷,一方面需要感情充沛,才能夠產生。
空間曲率的概念對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我從廣義相對論中知道所謂Ricci曲率的重要性。通過愛因斯坦方程,它描述物質的分佈,這個方程的簡潔和美麗使我詫異。我認為了解Ricci曲率是了解宏觀幾何的最重要一環,但幾何茫茫,無從著手。有一天很高興地發現Calabi先生在一九五四年時有一篇文章,敍述在複幾何的領域中,Ricci曲率有一個漂亮的命題,但他卻沒有辦法証明這個命題。當時我很興奮,但也覺得它不大可能是真實的,因為這個命題實在太美妙了。所有年青的朋友都是這麼說,甚至我的導師也是這麼說。
陳省身老師甚至認為這個研究方向的意義不大,我卻固執的認為對Calabi猜測總要找出一個水落石出的答案。直到有一天,經過大量的嘗試後,我才發覺從前走的方向完全是錯誤的,於是反過來企圖証明這個猜想。但要証明它,卻需要有基本的分析能力,我和我的朋友鄭紹遠花了不少工夫去建立跟這個問題有關的工作,終於我在一九七六年完成了這個重要猜想的証明。這個猜想在一九七六年全部完成,我同時應用它解決了代數幾何裏好幾個基本問題。毫無疑問的,這是一個漂亮的定理,也打開了幾何分析的一個大門。
當時我剛結婚,正在享受人生美好的時刻,也獨自地欣賞這個剛完成的定理的真實和美麗,有如自身的個體融入大自然裏面。當時的心境可以用下面兩句來描述:「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由這個定理引起的學問,除了幾何分析上的Monge-Ampere方程外,在代數幾何上獨樹一幟,以後在弦學理論成為一個重要的宇宙模型。
在解決Calabi猜想的同時,有一天我碰見到從前在柏克萊的同學Meeks先生。他是一個嬉皮士,兩手各摟抱着一個少女,在系裏的走廊上高高興興地走來。但我覺得此人極有才華,建議與他合作去解決一個極小流形的古老問題。我們用拓撲學的辦法解決了這個問題,反過來又用得到的結果,解決了拓撲學上一些重要的問題,再加上我的同學Thurston的重要工作,竟然解決了拓樸學上著名的Smith猜想。一九七六年可說是我收獲極為豐富的一年,我那年剛結婚,剛搬到洛杉磯,生活未算安定。由此可知,做學問不一定需要最安定的環境也可以成功的。
在代數幾何得到一定成功後,我接觸到很多代數幾何學家,也開始瞭解這個學科的走向。Calabi猜想是關於度量的猜測,我開始比較度量幾何和複纖維叢上的度量問題,我猜想纖維叢也有類似於Calabi猜想中的度量,同時和纖維朿的穩定性有關,Uhlenbeck和我花了很長一段工夫才將這個問題全部解決。﹙在這期間英國的Simon Donaldson用不同的方法解決了二維的情形,並且很快就完成了高維空間中這個定理的重要情形。﹚在完成這個問題後,我建議我的朋友Witten考慮這個定理的物理意義,他當時認為這個定理的物理意義不大,但一年後他改變了想法,寫了一篇文章解釋它們在弦論上的作用。直到如今,這個結構在弦論上仍佔據着很重要的位置。
這篇文章花了Uhlenbeck和我很長的時間,可說是極為艱苦的奮鬥才完成的。Uhlenbeck來Princeton訪問我時,為了尋找這個問題的解法,竟然關在房間裏三天之久。我和Uhlenbeck的工作以後被推廣,尤其是加上我的朋友Hitchin引進的Higgs Field以後,成為代數幾何和算術幾何中強有力的工具。Calabi猜想的一個重要結論是,代數空間有很強的拓樸限制,包括Miyaoka-Yau不等式的成立,從而有代數流型的剛性結果。這個結果被我應用而解決了古老的Severi猜想。在這個基礎上,我猜測某些代數空間有更一般的剛性結果。我並提出用調和映射的方法來解決這個猜想。
其實在更早的時候,我和Schoen已經在調和映射做了不少工作,例如在群作用的問題。當我向蕭蔭堂先生提出我的猜想和解決的辦法時,他開始時並不相信這個方法的可行性,但是他還是遁着這個路徑去解決了我猜想的一部份。以後Jost和我,以及蕭蔭堂和他的合作者們更成功地將調和映射應用到一些更經典的剛性問題上去。在一九八四年弦理論成為理論物論的重要一門學科以後,我以前做的好幾個工作都受到理論物理學家的歡迎。我也深受物理學家對數學洞察力的影響,我有十多位跟隨我的博士後,他們都是物理學博士。我從他們那裏學習物理。
最令我驚訝的一次是,我的博士後Brian Greene跑到我的辦公廳,向我解釋他最新的發現,就是在Calabi-Yau空間中,存在所謂鏡對稱的觀點,這個發現對代數幾何有極大的衝擊,影響至今。它的結論至為漂亮,從不同角度解釋了代數幾何裏百年來不解的現象,但物理學家沒有辦法給出一個証明,六年後在眾多數學家努力的基礎上,劉克峰、連文豪和我終於找到一個滿意的証明。但是我覺得我們對鏡對稱這個現象還是沒有得到深入的瞭解,兩年後Strominger、Zaslow和我終於找到這個對稱的幾何解釋,引起了一連串重要的突破,可是,鏡對稱在數學上到現在還沒有嚴格的証明。Zaslow是跟隨我的博士後,他以後成為西北大學的大教授。當時我和他還做了一個重要的工作。從弦學上膜的觀點,我們找到一個公式﹙Yau-Zaslow公式﹚。這個公式可以用來計算K3曲面上的有理曲線的個數,公式由數論中的某些著名的函數給出,這是數論函數出現在計算曲線數目的第一次,以後很多代數幾何學家繼續這個研究,將這個公式推廣到更一般的情形。
與物理學家合作是愉快的經驗,可以有跳躍性的進展,而又不停的去反思,希望能夠從數學上解釋這些現象,在這個過程中往往推進了數學的前沿。過去二十多年,我也花了一些工夫去做應用數學的工作,一方面和金芳蓉在圖論上的合作,一方面和我弟弟共同研究控制理論。近年來更和顧險峰等合作做圖像處理的研究。這些工作都和我從前研究的幾何分析有關,尤其是我和Peter Li研究的特徵函數的問題。起源於當年我在史丹福研究調和函數的梯度估計。我還記得我傍晚時躲在辦公室裏,試驗用不同的函數來算這些估值,捨不得去看史丹福校園落日的景色。
史丹福的校園確是漂亮,黃昏時在大教堂的廣場,在長長的迴廊上散步。看着落日鎔金,青草連天的景色,心情特別舒暢。我早年的工作都在這裏孕育而成。除了Calabi猜想外,還有正質量猜想的証明。七九年的夏天,我和Schoen住在他女朋友Los Altos的家裏,白天我們將這個猜想的証明逐步寫出來,到了晚上十時多才回家去游泳池游泳。在這一段日子裏,我們也將正數值曲率空間的理論完成。
丘成桐院士簡歷:
1949年4月4日出生於廣東省汕頭市。師事數學大師陳省身先生,為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史丹福大學、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現任哈佛大學講座教授。曾獲卡迪獎、威伯倫獎、數學界最高榮譽之渥爾夫數學獎、費爾茲獎、麥克阿瑟獎、瑞典皇家學院頒發之克瑞福特獎,及美國總統親頒國家科學獎等重要獎項。 為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海外院士、俄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以及義大利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同時榮獲多所知名大學的榮譽博士及榮譽教授。發表數百篇學術論文及著作,解決許多著名的難題,開創許多新的研究方向及領域。他的研究工作主導了微分幾何及其它幾個重要數學領域過去三十年的主要發展。他的工作改變並擴展了人們對偏微分方程在微分幾何中的作用和理解,並影響了拓撲學、代數幾何、表示理論、廣義相對論等領域。
維護單位:
新聞中心
更新日期:
99-06-08